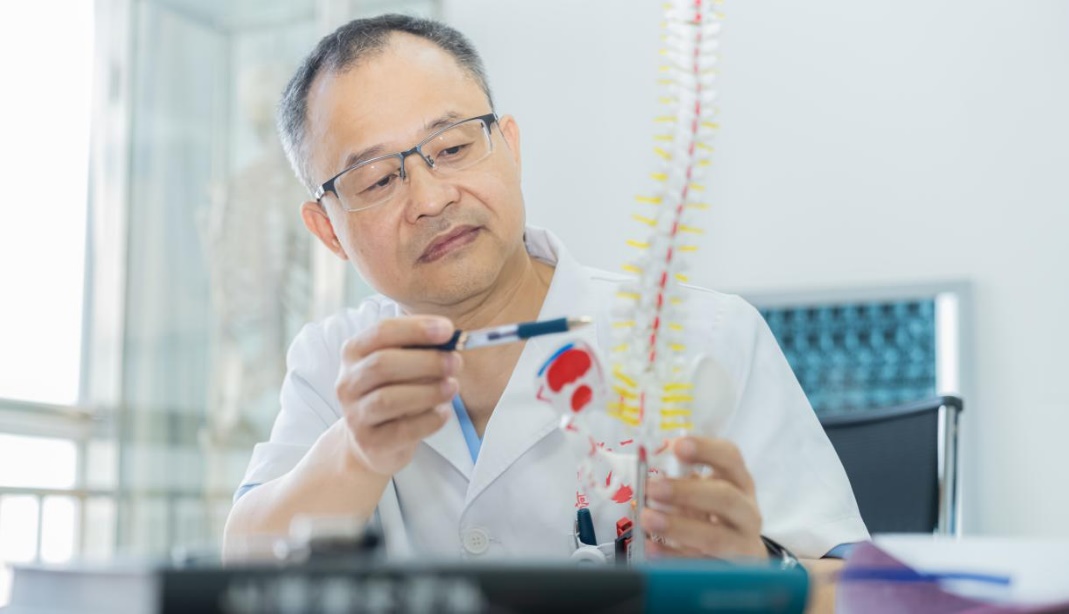在过去16万年的某个时间里,一个古代人类的遗骸最终埋葬在中国青藏高原的一个山洞中。也许那个人在那儿死了,或者一部分被它的亲戚或动物拾荒者拿走了。在短短几年内,肉消失了,骨头开始变质。然后千年流逝。冰川退缩,然后又返回并再次退缩,剩下的只是颚骨和一些牙齿。骨头逐渐被矿物外壳包裹着,这个古老祖先的DNA随时间和天气流失了。但是过去的一些信号仍然存在。
在人参牙齿的深处,蛋白质徘徊,降解,但仍可识别。当科学家在今年早些时候对它们进行分析时,他们发现了胶原蛋白,一种在骨骼和其他组织中发现的结构支持蛋白。它的化学特征是现代人类或尼安德特人的胶原蛋白中不存在的单个氨基酸变体,相反,它标志着颚骨属于神秘的人类素群Denisovans1的成员。在中国发现Denisovan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西伯利亚Denisova洞穴外发现的第一个人,此前所有其他同类遗骸都已被发现。而且该地点位于青藏高原上-海拔3,000米以上-表明Denisovans能够生活在非常寒冷,低氧的环境中。
但是这一发现也标志着另一个里程碑:这是第一次仅使用蛋白质鉴定出古老的人参素。
对于刚刚起步的古蛋白质组学领域,这是最惊人的发现之一,科学家在其中分析古代蛋白质,以回答有关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历史和进化的问题。科学家认为,蛋白质在化石中的停留时间比DNA更长,它可以使科学家们探索史前的整个新纪元,并使用分子工具来检查世界上比现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的骨头。
妈妈是尼安德特人,爸爸是德尼索瓦人:首次发现古代人类混合体
以前,科学家从180万年前的动物牙齿和380万年前的蛋壳中回收了蛋白质。现在,他们希望古蛋白质组学可以用于提供其他古老的人类化石化石的见识,这些化石化石失去了所有DNA的踪迹,从直立人到大约190万到14万年前在世界各地漫游,直到人类直立的弗洛雷西人。大约在60,000年前居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小型“ obbit”物种。通过观察这些蛋白质的变异,科学家希望回答关于古代人类群体进化的长期问题,例如哪些世系是智人的直接祖先。哥本哈根大学的生物考古学家马修·柯林斯(Matthew Collins)说:“泪水基本上可以释放出整个人类的树。”自1980年代以来,他一直处于这一领域的最前沿,当时该研究仅由少数研究人员组成。
时代的到来
尽管很激动,但有人认为研究人员可能难以从研究人员可以从蛋白质中获得的信息描绘出人类历史的确切图片,与从DNA中获得的信息相比,这是有限的。许多人担心,由于污染等问题,古蛋白质组学通常可能容易受到虚假结果的影响。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连大学的考古学家菲利普·斯托克哈默(Philipp Stockhammer)说:“渊博看到了非常好的研究,然后您看到人们发表非常奇怪的东西,因为他们对这些方法持批判性思考。” 。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从古代化石中提取的DNA改变了科学家对人类进化的理解。对不同人参素组DNA的相似性和差异的分析,使研究人员能够以以前不可能的方式绘制出纠结的家谱。遗传物质导致了一些重大发现,例如首先发现了丹尼索瓦人。
但是那张照片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DNA仅从三组人乳素中测序: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大多来自不到100,000年历史的标本(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一对来自西班牙的430,000岁的早期尼安德特人2)。再往前走几十万年,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模糊。哥本哈根大学的分子人类学家弗里多·韦尔克(Frido Welker)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令人兴奋的事情。例如,当丹尼索瓦斯(Denisovans)和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从世系中脱离出来时,这便成为了现代人类。但这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朦胧的一部分。例如,研究人员不知道是否存在于大约70万至0.000万年前的古老人类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是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祖先,还是仅尼安德特人的分支的一部分?韦尔克说:“许多事情是远古DNA无法实现的。”
追溯一百万年或更久,事情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楚。例如,直立人棉铃虫大约在190万年前首次出现在非洲,但由于没有DNA证据,目前尚不确定它与后来的人猿,包括智人之间的关系。
古代DNA也留下了地理盲点。DNA在温暖的环境中降解速度更快,因此,尽管在一个寒冷的西伯利亚洞穴中发现的具有100,000年历史的标本可能仍保留着遗传物质,但在非洲或东南亚酷热中度过了很长时间的化石通常不会。结果,对于来自这些地区的相对较近的人源蛋白(例如弗洛雷斯氏菌)的遗传知之甚少。
现在,研究人员希望蛋白质分析可以开始填补其中的一些空白。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早在1950年代,研究人员就报告说在化石中发现了氨基酸。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测序古老蛋白质所需的技术就不存在了。柯林斯说:“老实说,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真的相信我们将无法恢复古老的蛋白质序列。”
在研究人员意识到质谱(一种用于研究现代蛋白质的技术)也可以应用于古老的蛋白质之后,这种情况在2000年代发生了变化。质谱法本质上涉及将蛋白质分解成其组成肽(氨基酸短链)并分析其质量以推导其化学组成。
按DNA划分:考古学与古代基因组学之间的不安关系
研究人员已经使用这种方法筛查了数百个骨头碎片,以识别它们来自的动物类型。在这种称为质谱的动物考古学或ZooMS的特定方法中,研究人员分析了一种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成分的质量在不同的组和物种中有所不同,提供了特征性的指纹,使研究人员能够识别骨来源。
ZooMS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使用了3,从Denisova Cave的数千个碎片中鉴定出一个人骨,DNA后来被DNA分析显示是一个杂种,昵称Denny,有尼安德特人的母亲和Denisovan的父亲。伦敦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Francis Crick Institute)的人口遗传学家Pontus Skoglund说,即使仅凭这些结果,古老的蛋白质分析也已经大大扩展了我们对人类进化的认识。德国耶拿市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考古学家卡特琳娜·杜卡(Katerina Douka)现在正在使用该技术搜索来自亚洲的40,000片未鉴定的骨碎片,以期发现更多的古老人类。
但是ZooMS只能以广泛的笔触绘制图像。例如,一旦确定骨骼属于人参,就需要其他技术来深入研究。因此,其他人转向了shot弹枪蛋白质组学,其目的是鉴定样品蛋白质组中的所有蛋白质序列。蛋白质组的组成取决于所检查组织的种类,但通常会包含各种形式的胶原蛋白。Douka说,这种方法散发出成千上万的信号,这使其比ZooMS更具信息性,但解释起来也比较棘手。通过将这些信号与数据库中的已知序列进行匹配,研究人员可以确定样品中胶原蛋白或其他蛋白质的确切序列。
然后,科学家们可以将该新确定的蛋白质序列与其他人红素组的相同蛋白质进行比较,寻找单个氨基酸的相似性和差异,这将有助于将人红素置于家族树上。这类似于古代DNA研究人员如何看待遗传序列中的单字母变异。
填补空白
尽管研究人员之前曾将蛋白质分析与古代DNA测序结合使用,但西藏Denisovan是第一个古老的人类素,仅对蛋白质进行了分析,“其他人很快就可以追踪”(见“让化石说话”)。例如,观察海德堡嗜血杆菌的蛋白质序列,可以阐明其与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关系。
关于弗洛雷克斯菌的性质,辩论已经打了十五年,在2003年印度尼西亚弗洛雷斯岛上发现了这些遗迹。它与其他人源素的关系尚不清楚,暗示它可能是直立嗜血杆菌的矮小后代,甚至可能是它起源于与现代人类关系更远的南方古猿属。这个小组生活在200万年前,成员中包括著名的露西骨骼。
柯林斯说,蛋白质组学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完全相信我们周围有弗洛雷斯人蛋白质,该蛋白质可以测序,并且可以告诉我们在家族树中适合的位置。”另一个小人豆人吕宋人也是如此。它的骨头和牙齿是几年前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洞中发现的,并于今年早些时候报道了5。与弗氏杆菌相似,这些样品未产生DNA。奎松市菲律宾大学的考古学家Armand Salvador Mijares说,他正计划从发现吕宋草的洞穴中寄出Welker一颗动物牙齿,以测试分析古代热带材料中蛋白质的可行性。
随着研究人员准备对远古人类的蛋白质组进行更多的蛋白质组学分析,对其他动物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它们在较深时期的进化关系。
西伯利亚古代幽灵氏族开始交出其秘密
例如,在最近的一项分析中,哥本哈根大学的古蛋白质组学专家Enrico Cappellini和他的同事们使用蛋白质组学研究了灭绝的犀牛Stephanorhinus在犀牛家谱中的适合位置。根据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预印本6的报道,该团队能够从佐治亚州达马尼西(Dmanisi)残骸中提取蛋白质,这些残骸已有180万年的历史。氨基酸取代的模式表明该动物与已灭绝的羊毛犀牛(Coelodonta antiquitatis)密切相关。
藏族Denisovan的蛋白质来自牙本质,即牙齿内部的骨组织,而这些Stephanorhinus蛋白质则被锁在覆盖牙齿的牙釉质中。Cappellini建议,这对于发现非常古老的蛋白质可能特别有用。搪瓷是脊椎动物体内最坚硬的物质,被卡佩利尼称为封闭系统,可防止氨基酸浸出。这个有180万年历史的日期“ oesn”代表极限。他说。
实际上,其他人则走得更远。研究人员报告说,它们是从北极地区340万年前发现的骆驼中提取胶原蛋白序列的。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意大利都灵大学生物分子考古学家Beatrice Demarchi及其同事从一个380万年前的鸵鸟蛋壳中提取了蛋白质并进行了测序8。戴玛奇说,这种贝壳没有保存在一个寒冷的极地地区:它来自坦桑尼亚的一个地点,那里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8摄氏度。她说:“渊ou不会期望东西能在如此炎热的环境中生存。”她补充说,人乳清蛋白可能可以从相同的地方恢复。“必须尝试,我们吗?”?/ p>
出牙痛
在古代蛋白质使人类进化树的分支成为焦点之前,仍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到目前为止,研究人员已经能够相当容易地推断出古代人源蛋白的序列,因为它们已经含有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智人的DNA。这使他们能够预测可能出现在质谱信号中的蛋白质序列。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的古生物学家Svante P盲盲bo说:“渊源可以从已知的基因组序列中(无论是古代生物体还是现代人,找出您期望存在的片段,然后寻找它们)”在德国莱比锡。
但是,随着科学家们往后追溯,他们将需要在没有图谱的情况下计算出这些氨基酸的序列。P盲盲bo说,这是古代蛋白质组学的一个持续挑战,因为蛋白质被降解成小片段,并且样品经常被现代蛋白质污染。
柯林斯有信心做到这一点。他指出了他在2015年发表的论文9,其中他,韦尔克(Welker)和其他人为南美本地有蹄类动物绘制了系统发育树,这是一群看起来独特的哺乳动物,大约在12,000年前就灭绝了。由于无蹄类动物化石中没有可用的DNA,研究小组不得不从头开始对胶原蛋白进行测序,以将它们与其他动物的胶原蛋白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两个已灭绝的本土有蹄类动物,即Toxodon和Macrauchenia,与包括马和犀牛在内的一个群体密切相关,而正如一些研究人员所认为的那样,与包括大象和海牛在内的Afrotheria则不相关。
其他限制则更为根本。古代的牙齿和骨头含有少量蛋白质,因此可以用于识别标本的信息相对较少。例如,对西藏Denisovan的分析揭示了八种不同胶原蛋白的序列,总共略超过2,000个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中只有一种不同于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序列,将样品鉴定为Denisovan。这意味着,例如,即使研究人员能够对直立螺旋体标本中的蛋白质进行测序,氨基酸序列中也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明确说明其与现代人或古人类的关系。斯科格伦德说,相比之下,一个古老的基因组与任何其他基因组相比,都包含大约300万个变体,因此在进化方面的信息要多得多。
而且由于蛋白质通常执行关键功能“形成骨骼结构”,因此“它们”始终会随着物种的进化而发生很大变化。例如,对牙釉质特异的蛋白质在Denisovans,H。sapiens和Neanderthals中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用来区分这些基团。韦尔克说,但是,这些蛋白质在其他大猩猩中的确有所不同,并且在涉及较老的人红素组时可能会提供更多信息。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对古代人类群体中蛋白质序列的变化知之甚少。例如,科学家仅对单个Denisovan基因组进行了测序,这意味着为了鉴定藏族Denisovan,研究小组将蛋白质序列与该组中的另一个成员进行了比较。其他Denisovans可能有不同的变体。杜卡说:“任何遗传学家都对这种方法持怀疑态度,但是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在理解古代种群的基因组变异方面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
向过去学习
还有其他挑战。一些研究人员担心,围绕古蛋白质组学的广泛讨论可能导致该领域陷入与20年前的古代DNA领域相同的陷阱。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许多明显令人振奋的结果-例如,发现恐龙或捕获在琥珀中的昆虫的DNA,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污染或其他方法错误的产物。杜卡说:“如果蛋白质组学界发生这种情况,我不会感到惊讶。”
那些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人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许多研究人员正在共同努力,以创建一门强大的科学。其中包括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古学家杰西卡·亨迪(Jessica Hendy),他率先使用蛋白质来研究早期人类的饮食。亨迪和她的同事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从现代土耳其的alatalh枚玉树中发现了8000年历史的陶瓷中的蛋白质,这揭示了古代居民食用各种动植物,甚至将牛奶加工成乳清10。
亨迪说:“他的技术是如此有趣,令人着迷,并且确实引起了很多关注,尤其是现在。”她补充说:“确实需要谨慎行事。”Hendy与Welker一起是一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概述了该领域的最佳实践,从避免污染到在公共存储库中共享数据11。
亨迪补充说,需要对蛋白质如何长期生存和降解进行更多基础研究。她说,这类研究可能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可以使研究人员对其结果更有信心。她以Demarchi的作品为例:德玛奇发现,她380万岁的蛋壳中的蛋白质已与蛋壳中的矿物晶体表面结合,从而将其基本冻结在原位。亨迪说:“最酷的是,它实际上解释了蛋白质存活的原因,这使得发现更加可靠。”
即使仍有问题需要解决,该领域的进展也没有放缓的迹象。虽然人类进化可能会受到最广泛的关注,但科学家们正在以各种方式使用古代蛋白质组学,从研究古代牙齿牙垢中的疾病标记到研究使用哪种动物皮来制作中世纪羊皮纸13。
Demarchi说她为这一切感到兴奋。她说,在计算出已灭绝的生物的家谱时,蛋白质组学有可能掀起波澜。她说:“不要以为我会看到一生的终结。”“真的会很大吗?”
自然570,433-436(2019)